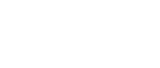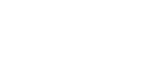【重磅 • 新作品读】 《百香》
| 招商动态 |2016-10-10
百 香(节选)
弋铧
5
这天吃过晚饭,老胡像往常一样巡视牧场和菜园。到底是冬季,日头下来以后就火速地有些冷意了。热闹过后,陡然清静下来,老胡还是觉得有点凄凉。他关照看守的雇工几句,往自己的院子走过来。
路径上有个人,渐渐地挪近。老胡有些诧异。
远远的一个小点,小范慢慢地在黑夜里移过来。老胡有少许吃惊,说起来,他和她算有点交情,有时候,他也会送她几把菜蔬,但仅此而已。
小范在刚起的月光里微笑着,慢慢进院门,径直往池塘那边的秋千上去了。老胡本来站在池塘边,又觉太过冷淡,忙拉把帆布椅也在池塘边坐下,离小范不远不近的距离。
小范话很少,老胡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有点风缓缓地从远山那边吹过来。两人空了一会儿,老胡便从右侧的鸭舍开始讲起,说到晚间会从山那边过来黄鼠狼,叼走他多少鸭子,还说到山那边爬过来的蛇,也把他的鸭给摆治了。
小范看看鸭舍:“现在有蛇在那边吗?”
老胡笑起来:“应该没有,不然鸭子没那么安静。”
小范说:“我家原来水缸里也卧过一条蛇,早上起来烧水,移开水缸盖,就见一条碗口粗的蛇卧在里面,我吓得大叫我妈。我妈生气极了,因为一缸的水都白白废掉,我和两个弟弟还得重新再去担水,得担好多担呢!”
老胡笑笑。
小范接着说:“我家门檐口还有燕子窝,总是叽叽喳喳的。家里人不许抄燕子窝,还有喜鹊窝,说怕散了福气。历来没抄过,历来也没见有福气。”
老胡只能不言语。
“胡大哥,你不是这里人。”小范瞪着一双黑眼眸,在慢慢明朗起来的月光里注视着老胡。
老胡突然警惕起来,不想再提起话头,他太清楚小范这类人的眼神了。曾经年轻时,他觉得女人只要年轻就可以,所谓秀色可餐。而现在,他挑女人,暧昧一下也未必不可,但是一定要和他能说得上话,不说读过什么《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者《尤利西斯》,而是至少能和他说到一块儿,有独立见解和思维,甚至能打动他,让他佩服。小范不是!他了解她们的眼神,那种媚气,从骨子里散发出来,有朝一日是要来索偿的。他太明白了。
天已经完全静下来,应该已经过七点了。老胡有点闷,不知道小范这样子还想待多久。凉意快速地升上来,变成飕飕的冷。老胡不禁打个寒颤,歪着头斜睨小范一眼,发现她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冷不冷?你要不要加点衣服?”老胡淡淡地问。他没有动弹一下的意思,冷漠的关心其实是想送客。
“胡大哥,我结婚后……”小范突然幽幽地传过来这么半句,戛然卡住。老胡没应答,因为不明白小范突然来这么半句是什么意思。“结婚有五年多了,老公挺老实,不知你见过没有?有时候会开辆面包车过来送货。”
老胡身子向后靠靠,想看看天上的星星,但只见寥寥的两三粒。
“我一直没能怀上孩子。看了很久的病,什么检查都做过,甚至,前段时间还做了试管婴儿。排好久的队,好不容易培育成功,真是好遭罪。但是没用,还是没怀上。”
老胡仍不言语,他的心在他的身体里咚咚跳跃,满脑子在转,小范想让他怎么样?
“人家说,老辈人传下的方子挺管用。我也是没办法,拖下去总还是要对你说,能行就算我积了大造化;不能行,就当我没说过。市面上多少钱,我一准儿按数付给你。或者,你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小范一直蜷在秋千椅上,老胡这才感觉到,自打上了秋千椅,她可根本没荡过,就那样一直把身子蜷在椅子里,好像要蜷回到生命最初的形状,回到母亲身体里。
老胡的神经一点一点地绷紧,他突然明白小范要什么了。他奇怪的是她怎么知道?她怎么看出来的?除了那头公鹿,还没有谁留意过呢,因为没显怀,谁能看得出呢?那天下午同学过去的时候,公鹿不就是为这个紧张?
老胡没动静。他的脸如果在白天的光线下看,已经非常变形,是的,当时如果再靠近一点,如果不是他高喊几声,他的同学就要走近那片危险领域,那是公鹿的底线,再近一点,他的同学就会遭遇鹿角毫不犹豫地顶峙,那简直不堪设想!
“可以吗?”小范声调降下来,明显带着怯意,但她坚持着,不能不说下去。
“我就想要鹿胎。你要什么价我都会接受的……”
老胡低沉地吼一句:“滚吧……”
“啊?”小范还没反应过来。
老胡站起来,嗓门提上去,但明显是强抑着:“你滚啊!”他的声音很凶恶,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颤抖。
6
老胡读书的时候算是学霸,考得也还不错,然而家境着实不佳,又因为是长子,和族中长辈商量许久,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师范。因为不光学费全免,而且每月还有补助,伙食和生活费再不劳家里操心,反而节省下来还有余钱支援老家。
分配倒也不错,去了某个省会城市的一类中学,教高中数学。他算是第一代有真正本科文凭的毕业生,在执教的中学,度过了尊师重教的第一个教师节。
他是任课老师,带三个高一年级——两个重点班,一个普通班,还没来得及成为班主任。学校挺重视他们这些分配来的大学生,分给小小的单身宿舍,对他们期望有加。教导主任让他们从高一带下去,带到高三这批孩子高考结束,然后再重新带一茬高一生,也这样过三年。三年三年地带下去。
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看着他们现在苦巴巴的样子,就想到自己曾经高中的苦。那时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入了大学校门,便成天之骄子,一切都觉得万象更新,前途似锦。
然而,人似乎不能有思想,想太多了,就觉得一切都特别空。看着手下自己教的那几个班,埋头苦学只望着高考这一个目的,任何时间和精力的浪费都是为顺利高考而埋下的障碍,老胡突然就觉得人生轮回的无意义。重复性的工作,重复性的日子,重复性的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接一个的三年,让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枉误。他手下的这帮孩子,所谓的学习,对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帮助和作用呢?老胡倒真是迷惑了。何况,他们考进大学,进入为世俗所艳羡的象牙塔里的生活,每天懒洋洋地混日子,只想修过及格线的学分,对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又有什么诠释的价值?
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从十三四岁,人就开始分类,起跑线就开始分岔,他觉得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不公平,一种当权者的无所谓的随意放弃,一种对别人人生的毫不在乎。
那时候南风渐盛,很多身边的人都开始辞职下海,老胡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一点意思也没有。他动了心思,想闯荡世界,证实自己的价值。
还算不错,他坚持带完他的毕业班,把这一届孩子们带到高中毕业,参加完高考。在毕业晚会上,他唰唰唰地给那些春风得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孩子签名留言,也和那些失意的没能进入大学接受再教育的孩子谈心。他说,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你总有发挥能力的机会。
然后,他义无反顾地走了。是自动离职——那会儿,国家干部还不允许停薪留职,他没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老胡和胡太是大学毕业后谈的恋爱,那会儿世风还好,感情也真实,老胡说声辞职,只身南下,胡太后脚就跟过来,打出一番天下。
老胡自己也没有想到,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满腹的微积分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最后却搞上最不需要动脑子的行当——一个从农村过来务工的初中肄业生都能从事的行当。
装修这买卖,和人打交道打得多,业务做大以后,便不仅仅是家庭装饰装潢了,而是直奔大客户,满楼满盘地拉订单。老胡的日子从那时候起节节升高,老胡的病也是从那会儿落下的,紧张,难受,恶心,呕吐……什么大医院都查过,酒也戒了,烟也戒了,除了他们这帮人最易得的“三高”,却还是找不到别的病根儿。医生越查不出什么,老胡就越是心慌,觉得自己大事将近。颓靡过后,反倒没什么牵挂,慢慢地,就把生意移给一直做着公司总监的侄子,让满心牵挂生意的妻子当老板,他自己淡出江湖了。那时候,竟然被人介绍去终南山,还修行了半年,差点再不归俗。
当时儿子还在读初二,正是关键的年龄,胡太逼得急。想她一个女人,又管家又管生意,还摊着这样的丈夫,到底不易。胡太就托关系,在罗家嘴这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的地方给丈夫买了块院子,让他在这边安心修性。
老胡也没想闹腾多大,可能稍有点出世之心,觉得有这么块地方怡情养性,最主要是把身体修整好,挺不错。这便是百香的雏形。
后来,他竟渐渐痴迷于此,不仅把院子扩张了二十亩,还租了两百多亩更大的地皮来饲养大型牲畜。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小时候在老家一样,翻养田地,与牲畜相伴,与植物菜蔬为友,跳到塘里与鱼儿嬉戏。远山是他的尽处,大且神秘,可能没有狼,但有野猪、野鸡、黄鼠狼,甚至果子狸,还有各种有毒无毒的蛇类、爬虫类。他断了烟,却没戒酒,长期素食,只吃自己种养的这些蔬果,每天在这片大自然里生活,体质慢慢好起来,“三高”降下,所有的症状竟然烟消云散。老胡想,他又回到他童年的日子,转一个圈,落甲归田。人生的轮回,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从湖北老家到陕西上大学,从陕西大学毕业到分配去山东教书,从山东辞职再到广东下海。广东待的地方太多了,一会儿茂名,一会儿韶关,一会儿英德,他后来定性,把公司固执地开在深圳,把家也完完全全地安在深圳,落在深圳户籍上,买下三套房。现在,他又跑到深圳的邻市来,他的下半辈子,就决定在这百香过下去。
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奇怪。是的,百香的日子和他小时候的日子几乎没有区别,硬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可能百香比他的家乡还是富裕得多。也许在老家,他会驰骋得更远些,甚至可以带动他的乡亲来建设一片比百香更大的田园和牧场,有什么难的?现在他有的是钱,足可以使性子乱花的钱。然而,他没有,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回自己的家乡,去弄这样的一片地方。人是多么奇怪,在异乡过着怀念故乡和童年的生活,却坚决不愿意回到曾经的故土,去免却念旧思乡之苦累。
老胡不想解释,不想探究。人,是很奇怪的动物,比他饲养的那些牲畜复杂得多。
只是,很多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忘记他曾经满怀豪情斗志昂扬地教过的那些学生们,他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长相,他们的性格,那些孩子们之间的友谊和个中的小矛盾……他一直记得。
他再也没有和他的学生们有过任何联系。他知道他们有的人会很杰出,有的人会很平庸,有的人也许会长寿,有的人也许会命运多舛。像他一样,总有经过和阅历,总有失败或成功。
他把他们的名字放进他饲养的那些牲畜中,刘玉华、曾志勇、薛青、李纯浩、钟声……
他对它们像人类一样地尊重,像他带过的学生们一般心疼。他和它们讲悄悄话,掏出它们的心思:谁和谁闹别扭,谁和谁拉帮结派,谁喜欢打小报告,谁阳奉阴违,甚至,在“毕业”后,谁有可能和谁谈恋爱,谁和谁修成正果。它们会向他诉不肯向别人诉的苦,流不肯向别人流的泪,告诉他不肯向别人告诉的愿望,向他吐露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的野心。比如,刘玉华暗示他支持它,去做所有小母牛们都会讥笑它的事情:它想去追求那个俊朗健康的曾志勇;钟声却叫他给它勇气,去与全世界都认为比钟声厉害的那头最强健的巴马香猪严宏忠去争个高下……
他知道它们的将来,就像他早就知道他的那些学生们的将来一样,进入社会,或者进入屠宰场,人和牲畜一样,都是宿命,有逃不过的命运。但只要现在,在活的时候,努力地,坚持地,快乐地活。在阳光下跑,在雨天里泥泞,在风里厌世,至少健康地,被尊重地,活过这么一生了。
然而,他从来没想过,他的学生里,会不会有个小范这样的人?他其实压根儿都不了解小范,可是他的学生里,会不会总有一个像小范这样的,没太多的文化,远嫁到岭南一个不算富裕的小村里,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当地人成了家,开一爿小店,每天最发愁的事,就是如何为这个陌生的家族传宗接代?
老胡吹了一会儿风,把通向大平台的铁门牢牢锁住,踏着台阶下了平台,慢慢地踱回自己的南边住处。
西里在院口等着他,他唤它几声,锁了院门。西里又随着他看周边饲养的那些牲畜:两个池塘的鱼都没什么动静,后院锁着的那些鸭也没闹腾了,那些宝贝鸡也进笼熟睡了。西里没有阿妹聪明,原来老和可可在一道儿,哥儿俩凶神恶煞,很是张狂过一阵子,后来阿妹没了,把它哥俩分开,多少有些孤单。老胡看看西里瞅着他的眼神,叹口气,他知道它的孤单。
刘布头和老婆早休息了,另几个看场的员工也早躺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青草的香气。老胡最后检视下自己的院子,捏捏锁头,又踱回池塘边。
一忽儿,恍然觉得一千年好像就过去了,抬眼借着一点半明半暗的天光,才知道只过了二十多分钟。已经八点三十二分。
老胡起身,把西里放进院门边的窝里,慢慢回到自己的房间,关掉手机。
7
隔了几天,罗村和罗书真带着人来百香,介绍说是开电子厂的彭生。彭生也是深圳过来的,眉眼间气宇轩昂,听村长介绍老胡是百香的园主,便对老胡特别客气。
罗村介绍说:“彭生是湖北的,也是你们老乡。”
老胡笑笑:“岭南两湖人多,不过名声不好,说我们太贼精,是吧?”
彭生笑:“深圳蛇口那边的湖北人更多。胡总在深圳住哪里?”
老胡说:“住福田。现在很少回去,已经习惯这边了。”他接着解释,“我现在是扎根这里,都办下这边的户籍了。”
罗村忙点头:“那是,如果不是罗家嘴的人,是买不了这片地的。”
彭生问一声:“当时是多少钱一亩?”
这话问得稍显突兀,罗村、罗书、老胡,都尴尬地支吾过去。罗村忙介绍老胡的百香,简直就是大众嘴里的生态园,新鲜无害的果蔬,自然放牧吃草觅食的牲畜……
彭生说:“那太好了,我以后在这边做工厂,可以每顿吃上天然食物。现在,这吃,实在是太重要了!”
老胡蓦地一愣,转头问罗书:“这话我怎么没听懂?”
罗书顿了顿,说:“百香西边的几百亩荒地,彭生想租下来开工厂。以后,你们可是邻居。都是湖北的,家都住深圳,产业都在我们罗家嘴。来,以后大家都是亲戚!”罗书笑笑。
老胡声音重起来:“百香西边的地,不是说一直没人要吗?土质又差,也不好引水,电就更不要谈了。电都没办法解决,哪里能开什么工厂?”
彭生有点奇怪:“我们是开电子厂啊,胡总不会以为我们影响你的生态园吧?电子厂没污染的。”
罗书说:“如果他们租地盖厂房,报到乡里去,供电的问题会马上解决。乡里现在就是要发展,就是想招商引资,如果有这类项目,倒好批下来。那时,胡总你的供电问题也解决了。”
老胡正色起来:“开什么工厂?那不把我的百香全给毁了?有工厂的地方,哪可能再有什么绿色食品?你们想想,废气、废水、废渣……嗐,这些牛、这些鹿、这些猪、这些羊,它们还能生存下去吗?”
彭生小声地辩驳起来:“我们是电子厂,哪有什么废气、废水、废渣的?”
老胡明显有点生气,不再理人,面朝着远山。
大家安静一会儿,罗书接口:“胡总啊,我们罗家嘴是穷地方。全国都说岭南富,可是到我们这边,富得也就只剩青山绿水了,富得那叫一个干净!”
罗村没再插嘴,安心地听书记讲话。“我们地理偏,往前面十几里地,说是廖仲恺先生的祖籍,谁知道呢?也没听说他后来来过一天没有!建高新区,没我们的份儿;建旅游区,也没我们的份儿。没特产,也没温泉,更没异象。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红红火火,岭南着实闹腾得风生水起。可是不管政府做什么,我们连擦个边的份儿也没有。就好像,我们被忘记了。通高速,整高架,修高铁,全离我们远远的,到我们这儿,您若不自驾车,还真得坐辆“随手招”到二级路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进来。我们现在有的也就是这片土地,荒郊野岭的,不然,胡总也不会看上我们这地儿,过您说的神仙一般的日子。”
老胡笑起来:“哪里有你说得这么荒凉?就我这边靠近那片山,有点野,可能离大道远,政府规划不到这里罢了。你们那边,还好。”
罗村说:“哪里,要是政府规划到我们这儿,我们早就农转非了,早就像别的乡、别的村一样,成工业园了!”
老胡冷笑一声:“政府都规划了,还有农牧业没有?我们到底是农业大国,还是得吃粮的。”
罗书淡淡地说一句:“我们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怎么也得认命。但人活着,也得有希望。为什么一样是农民,人家可以富得流油,再也不用靠天吃饭,我们就必须守着这片地,去种他妈的什么粮?”这话有点粗口,老胡、彭生虽然是生意人,但都斯斯文文,粗口对他们好像不太妥,但罗书讲完,很正义凛然的样子。
“祖宗留给我们什么,我们认什么!有的祖宗留下好风水,后世得到便宜,那是人家修的福分,再什么羡慕嫉妒恨,也没办法!祖宗留下地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经营,那我们这一代,尽量过好,不行吗?”
罗村又接上去,赔着笑说:“主要是这样,如果开电子厂的话,我们村里的富余人员也有活儿干了,不用千山万水地往深圳广州外省跑,正正经经地在家门口,靠薪水也能吃上饭。”
老胡心里冷笑,他在生意场上多少年,太知道这些出售土地的农民了。还想干活儿?简直是痴人说梦吧?大把的土地卖给工厂,这辈子把下几辈子的利益都得完了。但是他不好再言语,毕竟,地是人家的。想来刚才罗书、罗村也早带彭生看过那些废弃多年的荒地,也许还不只一次。今天介绍彭生过来认识,也只是表面上的礼貌,人家的土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犯得着向老胡解释什么吗?
老胡不吭声,一肚子怒海翻江。
这当口,看鹿的乔师傅急忙忙跑过来,说叶月红有点闹腾,有两天没吃东西,老胡急着他的鹿,倒打破眼下大家的尴尬。罗书、罗村带着彭生先走了,老胡便和乔师傅朝鹿场那边去。
乔师傅看模样大约六十岁,有只眼睛好像有点白内障,裹一层白霜似的,长得不高,穿得却干净。当时过来的时候,乔师傅说自己原来是三峡那边的,后来移民到枝江,一直没怎么适应,再后来就和老伴一商量,跟着儿子儿媳一块儿到岭南来。他当时来百香应聘的时候,说自己身体还棒,但是这边活儿不好找,像他这般岁数的人,找了半年没活儿干,也急。
乔师傅挺会说价,把自己的工钱要求到三千元一个月,还得包吃包住,周日另外休息一天。因为家里人都这个时间休息,还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总得享点含饴弄孙之乐。
老胡倒都答应,仔细说了是十六头鹿——十头马鹿,六头梅花鹿。
乔师傅不木讷,毕竟走了些地方,见过世面。说起三峡移民,老胡以为他会很怀念原来的家乡,到底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说搬迁就搬迁了?
“那有什么可怀念的?原来的地方可苦着呢,和这边没法比,和枝江也没法比。”乔师傅倒嗤之以鼻。
“哦?”老胡有兴趣起来,“可是那么多风景都给毁了,神女峰也没了。我还专门在三峡大坝建成之前跑去看了那些风景呢,想想都可惜!”
“那有什么可惜的?”乔师傅大手一挥,“那些风景一点用处都冇得!”他兴致上来,讲了许多建大坝时的趣闻,截流时的惊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老胡不吭气,心里可惜着毁掉的那些风景。乔师傅倒越发措辞激烈:“那些都是没用的文化人搞的事情,他们吟风吟月,坐高级轮船逛几圈,又回他们的好日子去。可是他们不想想,我们在那里苦巴巴地过了上百辈子。修水电站,修大坝,造福于民,知道吗?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为什么让我们守着风景去过无水愁电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老胡便只能笑笑。老胡和乔师傅到了鹿场,叶月红还在害喜的阶段,又是初胎,胃口有点娇气。老胡就让乔师傅给叶月红多掺点黄豆和麸皮,又仔细看看那些鹿们,叮嘱乔师傅,那头雄鹿过段时间要锯茸;那头鹿别看个头小,脾气倔强着呢;那头母鹿最近有点受风,让它在阳光下多晒晒,给它喂点苔藓类的植物。
乔师傅嘀咕说:“我都不知道南方也能养鹿,以前以为只有北方产鹿,而且还以为梅花鹿是稀罕动物呢。”
老胡说:“这边养下的鹿肯定没有北方的好。不过,只要地界儿开阔,鹿群还是可以适应的。野生梅花鹿和马鹿确实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但人工饲养的话,也就没那么些说法。”
乔师傅比雇的另几个看工话多些,可能以为自己走南闯北有些见识吧:“鹿的全身都是宝啊。你还可以把鹿肉制成鹿干卖呢。清远还是哪里,我听我儿子朋友说的,有片很大的养鹿基地,一年下来,很赚钱的。”乔师傅一直对赚钱有很大的想法,描绘了好半天养殖的美好前景。
老胡只想了断和他的对话:“鹿和牛啊,羊啊,猪啊,都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帮人家代养的,收点代养费罢了!”
老胡交代完事情,马上走掉了。
(《百香》,中篇小说,原载《清明》,2016年第五期,责任编辑:刘鹏艳)
 招商热线:400-151-2002
招商热线:400-151-2002